【文学评论】巴黎,多少爱情假汝之名以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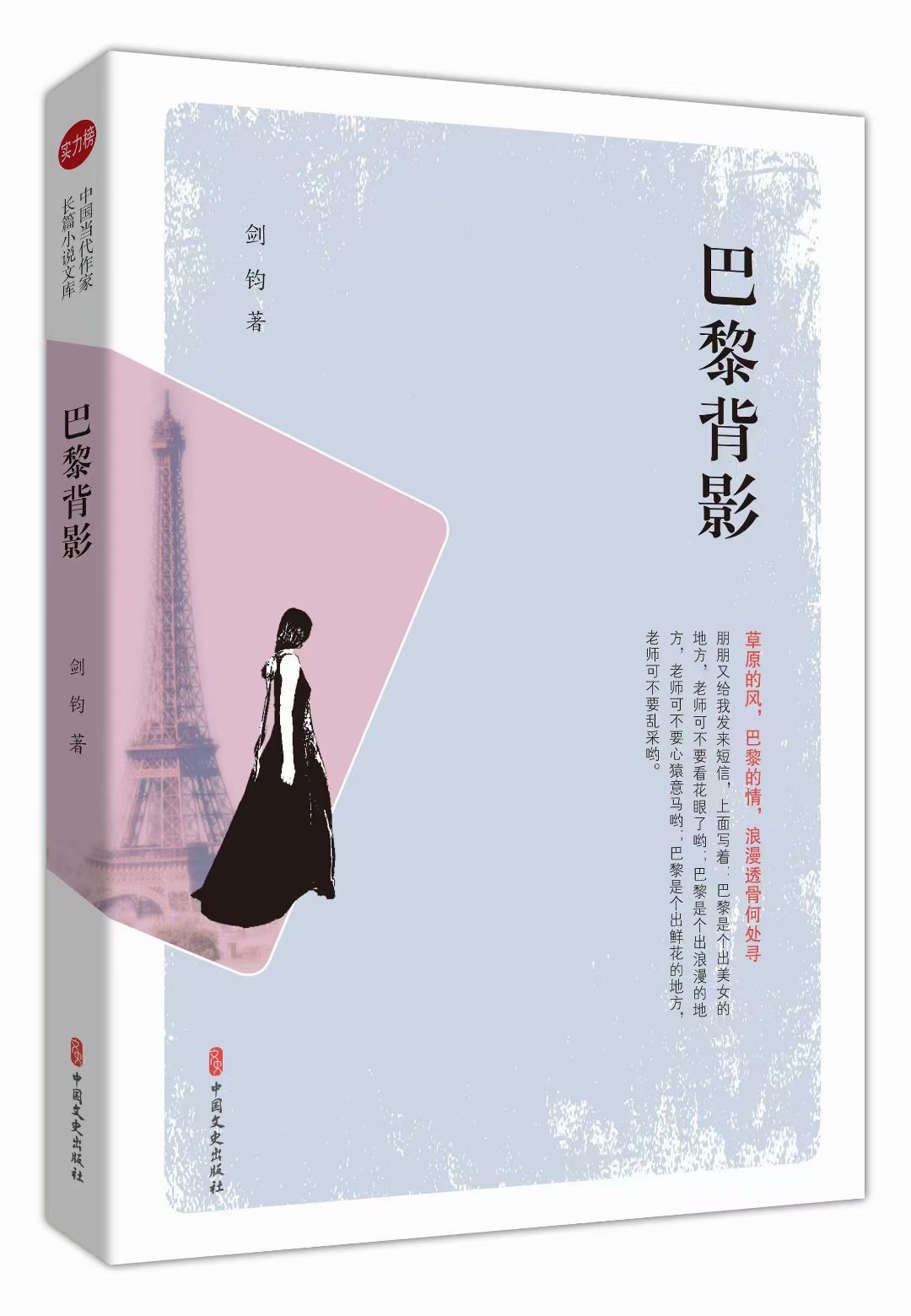
作者:甘 周
刚拿到作家剑钧的爱情小说《巴黎背影》,相信很多人跟我一样,不禁想问一句:为什么是巴黎?
或许靠爱情维持生命的包法利夫人知道答案,她说,巴黎是“无法衡量的名声”,听到巴黎这个名字,耳边仿佛响起了教堂的钟声,眼前好似看到一束光芒。这钟声与光芒是如此诱人,以致在小说《白痴》里美艳的娜斯塔霞失踪后,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她的茶几上摆了一本打开的《包法利夫人》。
从巴黎的爱情灯塔发出的光芒穿过法兰西的天空,照亮了欧洲,也照亮了全世界。
巴尔扎克说过,巴黎的爱情不同于任何一种爱情。巴尔扎克、雨果、福楼拜、大小仲马、司汤达、左拉、罗曼·罗兰……这些举世闻名的文学巨匠共同订立了爱情王国的法典,修建了浪漫爱情的灯塔,吸引着世界各地的善男信女到巴黎朝圣。如今,面对塞纳河的波影,爱侣们把刻着他们名字的同心锁挂在“爱桥”的栏杆上,然后将钥匙抛入水中。在巴黎宣誓爱情的忠贞,仿佛比山盟海誓还要坚固可靠。你可以怀疑爱情,但你不能不相信巴黎。
因此,当剑钧把距离巴黎差不多有一个欧亚大陆那么宽的科尔沁草原上的爱情故事与爱情之都联系在一起的时候,请你不要怀疑自己的眼睛。出现在《巴黎背影》中的形形色色的人物,无论性别、肤色、职业、年龄,可以说个个都是爱情王国的合法公民,剑钧让他们游荡在巴黎圣母院里、徘徊在塞纳河畔、相遇在没有奶茶的咖啡馆里,就是为了把这些在爱情世界里丧失理智的人带到爱情的圣地,让他们面对那些圣所,重新审视他们的爱情并做出抉择。
流浪诗人巴音孟和与小说作家霍日查宣称从雨果的《巴黎圣母院》里接受了爱情的启蒙,都把美少女萨日娜当成了他们的埃斯梅拉达,一旦爱情失利却都不由自主地从替补者身上寻找安慰;柳玲玲,留学巴黎的江南才女,在遭遇了突如其来的家庭变故后期盼着她的卡西莫多,竟阴差阳错陷入暴力狂的虐恋。围绕这四个痴男怨女的爱情纠葛,作者引入了其他十多个相对次要的人物,比如哲学教师枫、枫的爱人云、霍日查的同学尹骅、女学生朋朋、女作家虹、柳父、柳的男友大卫、商人夏小芸,等等,不管这些人物的身份差异有多大,人生经历有多复杂,甚至行事有多不堪,他们都带着自己的爱情故事进入到我们的视野里,与作为讲述者的诗人和作家在巴黎相会,并陈述自己的爱情纠葛。
《巴黎背影》里几乎没有一个纯正的法国人。为了把这些人物引到巴黎来,作者充分激活了主人公的社会关系,借助互联网、手机等现代通信工具及各类交通工具,将各类人物织进一个庞大而结实的社交网络中,随着两位叙述者的活动轨迹,这个网络从科尔沁草原一直延伸到法兰西首都。因为作者精心设计的人物关系与故事结构,《巴黎背影》中的本土爱情故事与巴黎发生了实实在在的联系。在万里之遥的法兰西首都,沐浴在爱情圣地的浪漫之光里,老祖母湮没在岁月深处的跨国爱情重新被唤醒,年轻一代的爱情与老祖母的爱情对照,草原的爱情与巴黎的爱情对照,由此,现实中那些剪不断理还乱的情感纠葛逐渐变得清晰,迷失的人开始找到回家的路。
“有人说,恋爱是一种病,得了便会丧失理智,恍恍惚惚,会做出许多匪夷所思的事儿来。”剑钧为《巴黎爱情》写的这个开头似乎是为了呼应雨果在《巴黎圣母院》里对爱情的定义:“爱就像一棵树,它自行生长,深深地扎根于我们的内心,甚至在我们心灵的废墟上也能继续茁壮成长。这种感情愈是盲目,就愈加顽强,这真不可思议。它在毫无道理的时候反倒是最最强烈。”爱情始于欲望,发自本能,但爱情又试图超越欲望,高出本能。爱上埃斯梅拉达的所有男人都声称他们的爱发自内心真诚不虚,然而,只有卡西莫多愿意为埃斯梅拉达献出一切,这份感情或许是冲动盲目的,但它具有无目的的合目的性,奇丑无比、地位低微的卡西莫多借此超越了身形俊健、位高权重的竞争者,从情人的目光里进而从自己的内心深处提升了自己,达到了精神与肉体的和谐圆满。从这个意义说,爱情未尝不是一种世俗的宗教。那些试图超越本能与欲望又不愿放下肉身的人,终究灵肉两失,反倒成了本能与欲望的奴隶。
东方女诗人蓝萌萌与苏格兰诗人的爱情在塞纳河左岸浓郁的艺术氛围衬托下,显得美好而浪漫,仿佛抒情诗一般柔美。然而,面对无情的战火,苏格兰诗人退缩了,他不但拒绝护送爱人回归祖国参加救亡,而且剥夺了她做母亲的权利。当绝望的蓝萌萌纵身跳入塞纳河中的那一刻,她的爱情与诗才也坠入了水中,那被人救起的是莎仁托雅,而非诗人蓝萌萌。
文章来源:《文学评论》 网址: http://www.wxplzz.cn/zonghexinwen/2021/0323/705.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