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评论|用诗歌的方式存储“光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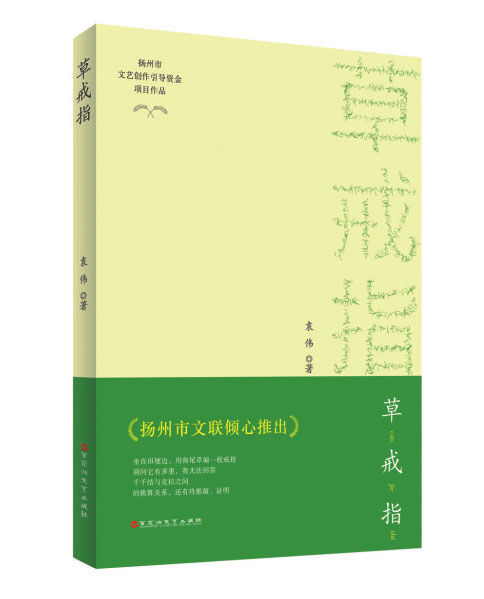
??作者:扬州大学文学院2020级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研究生?邱奇豪(24岁)
2018年盛夏,袁伟推出了个人的第一本诗集《栽种春光》,用诗歌的形式,真诚地书写着自己的乡愁和本科生涯的所见所感。作为一名农学生和贵州印江的“苗人”,他很自然地把思维的触角伸向了自己整日耕耘研究的试验田和近在眼前却远隔千里的故乡风物。以“每栽下一株秧苗,就给水田鞠上一躬”,认真雕琢自己的每一篇诗作。历经了又三年的沉潜之后,袁伟又赶在自己研究生毕业之前,推出了个人第二部诗集《草戒指》。
《草戒指》相较于前作,无论是诗集的编排还是诗歌的内容,都更加成熟和从容。经验的累积和视野的开阔,让袁伟的诗作有了更多的可能。从《栽种春光》到《草戒指》,在“乡愁”、“爱情”、“离别”、“社会观察”等一般主题之外,袁伟诗歌创作还存在着另一种母题指向,即对“光热”的追寻。正如凡·高近乎疯狂地涂抹心中的向日葵、歌颂光与热的生命一样,“羞于表达”的袁伟也在创作中,孜孜不倦地探寻以诗歌的形式存储“光热”的可能性。从诗集《栽种春光》最后一篇同名诗中“我在立夏后的田里栽种春光”,到《草戒指》开篇《取样》中“金色的稻浪”“腹中都装着光温水热”,可见两本诗集的接续和其诗学理念践行的一贯性。
“趋光热性”的形成
在《草戒指》第一章的《蝼蛄》一篇中,作者对于蝼蛄这一“试验田里的恶害”,不乏同情与敬畏。它们“在烈日加热过的最后半截光阴中,审视自己的一生”。对热与光的追逐,虽然是以付出生命为代价的,但它们仍义无反顾。
清晨的菜地里,一群蚂蚁
正在参加某只蝼蛄的出殡仪式
昨夜,月光曾拿出所有亮度
用古老的温柔诱杀了它
趋光性,是它自撰的墓志铭
——《蝼蛄》
由这首诗,便引出了两个重要的概念——“趋热性”与“趋光性”。因为长期从事农学研究和实践,袁伟对于这些概念,可以说再熟悉不过了。在长期的观察研究中,他将这种动植物对光热刺激的敏感,移情与内化,逐渐形成了其诗学风格的“趋光热性”。如在《山坡橘》中,“橘子里积淀的阳光,替你解开群山的枷锁”;在《晾衣架》中,“他用宽厚的肩膀挑起沉重与湿气,为我换来最原始的光合养料”;以及在《拾穗》中,对于“一颗稻子是伟大的,它所孕育的春光,足以帮助自己唤醒沉睡的青春”的歌颂和“叩谢恩光”……
沿着袁伟的诗歌创作与成长轨迹看去,这种“趋光热性”的诗歌向度的形成,主要源于以下方面:
其一,是专业研究的本能。“在实验田里待得太久”,他不自觉地“沾染许多作物的习性”(《草戒指》),而这其中除了“木讷”,“趋光热性”也不容忽视。《草戒指》相较于《栽种春光》,对于农事活动的相关书写,无论是在篇幅还是细腻程度上,都有了大幅增加和提高。其中,对于植物生长过程中的“光合”作用,更是倾注了大量的笔墨。正是对“光合”作用使“一颗谷粒的生命也有深度,厚度和宽度”(《考种》)体会至深,作者才会有如以下诗篇中的共情与思索:
?生活也是一轮红日
但却很少有人敢赤诚面对
一出一落,生命已错过
无数次灌浆和充实的时机
——《定日镜》
其二,是其个人成长的经历。因为父母长期在外务工,袁伟在上大学前的生活,只是一连串若即若离的地名。漂泊,是其生活的常态。《生僻字》一篇,便是他在漂泊之中,身份模糊的一个写照——“自从走出字典后,许多伙伴都失去了原有的姓名,我们像一群劫后余生的灾民,在不同的读音中继续逃亡”。不安的状态、在融入与割裂中不停转换的环境,使其形成了孤独、敏感的心绪。对于性格本身来说,这是消极的。但对于诗歌创作来说,它却使袁伟对于光与热的体察更为敏锐。对于光与热的刺激,能够及时反馈和报以歌颂。
在《西风烈》一篇中,袁伟把扬州冬天的冷气,比作脱缰的野马——“昨夜,它用铁蹄踏破了宿舍的玻璃窗,耳边此起彼伏的嘶鸣昼夜未停,原以为晒过的被子,已储存了足够的阳光,牙关却仍声声作响,连阳光都勒不住的狂野,就更不能苛责月光多么无力”。而他,只能借助在故乡习得的饮酒习惯,才能抓住牵制“这匹野马”的缰绳。在严寒的拷打之下,作者对于如盛夏试验田里的光与热,无疑更加珍视与渴望。
文章来源:《文学评论》 网址: http://www.wxplzz.cn/zonghexinwen/2022/0108/908.html
上一篇:文学评论|温暖的底色,时代的印记
下一篇:2021//我的文学梦想在齐鲁壹点绽放